系列文章超連結:
--------------------------------------------------------------------------------
【篇一】 【篇二】 【篇三】 【篇四】 【篇五】
--------------------------------------------------------------------------------
文/馮天瑜(武漢大學教授)
四、清軍進攻漢陽,民軍從武昌偷襲漢口失敗
據馮國璋(1859-1919)的參謀長張聯棻(ㄈㄣ)在《記辛亥武漢之戰》一文中說,10月29日起,由馮國璋負責漢口前線戰事。11月21日上午七時,清軍一個混成協由蔡甸渡河,向漢陽進攻,民軍無力阻擋,退守三眼橋。同日下午八時,黎元洪根據姚金鏞、賓士禮二人報告,向民軍發出命令:「我軍擬陸海軍並進,由青山附近渡江,先占漢口諶家磯,然後向劉家廟滿軍施行攻擊。」其中陸軍進攻的主力為成炳榮率領的第三協。給成炳榮的命令,由姚金鏞、賓士禮送往,並指定二人幫同籌畫。給海軍司令湯薌銘的命令,由徐達明、吳兆鯉送往,並令二人留艦參戰。
負責率步兵、工兵由武昌渡江襲擊劉家廟的第三協統領成炳榮,曾留學日本士官學校,原在清湖北督練公所任職,是一昏聵的酒徒,武昌起義後,被裹脅加入民軍,這次受命渡江襲敵,十分畏懼。姚、賓二人向成炳榮詳細交待任務後,即返回漢陽。22日晚,成炳榮率部出發,開始誤朝武昌方向進發,發現走錯以後,再折向青山江邊乘船,在海琛、海籌兩艦掩護下,在漢口郊區登岸。向諶家磯進軍,行抵三道橋時,因大水初退,泥深不能立足。橋頭清軍發現民軍襲來,猛烈開火,民軍不支後撤,沿原路退到江邊乘船回青山。成炳榮本人出發前曾大量飲酒,在青山登船時已酒醉不醒,未同部隊一起過江,部隊失去指揮,其敗績是不可避免的。

▲被革命軍抓獲的清軍偵探
11月24日,軍政府復令成炳榮所率第三協渡江由五通口進攻。李作棟持都督令箭前往督戰,成炳榮以為將問昨日之罪,聲言「與其軍前行刑,不如水中自盡」,即自行投水。後被救起。其部屬標統劉廷璧、胡廷佐都說他神經失常,建議以後再論。李作棟臨時決定,軍事行動由劉、胡二人負責。部隊倉猝登舟渡江,行抵五通口。清軍因前日遭到偷襲,此時早有準備,民軍在開闊地帶受到清軍機槍掃射,後退至三道橋附近蘆葦叢中,與清軍相持三個小時,民軍犧牲三百餘人,五通口不能立足,仍渡江返回青山防地。以後,成炳榮被撤職。
從青山渡江偷襲漢口,未嘗不是一著好棋,清軍對民軍的這一動作十分害怕,馮國璋得知民軍從青山渡江偷襲後曾驚呼:「兵力漸薄,被匪抄我後路,雖分兵抵禦,如無援軍速來,萬難久持。」可惜民軍這一奇襲行動委之成炳榮這樣的怯懦庸才指揮,當然只能以失敗告終。
五、漢陽戰場的往復拼殺
在民軍偷襲漢口的前後,漢陽戰場進入白熱化階段。
11月21日,由蔡甸進犯的清軍已推進到距三眼橋不遠處。黃興派祁國鈞率一營增援三眼橋一線民軍守軍,經徹夜激戰,至11月22日上午,清軍漢口炮隊向鍋底山、仙女山猛烈炮擊,民軍被迫退至山麓抵抗。另一部敵軍攜機關槍由彭家嘴徒涉,向防守三眼橋民軍側擊。
民軍標統祁國鈞受重傷,湘軍第二協和鄂軍,退守鍋底山、花園一線,黃興聞報,即命步隊第四協以一標增援,武昌亦加派第十四標和第三標渡江助戰;清軍亦大量增加兵力。民軍往復拼殺,美娘山未奪回,仙女山又失守。戰至夜七時始停。各部隊奉命後,均嚴為防禦。第七標統帶胡廷佐當命第一營管帶左國棟率該營於晚八時襲擊仙女山之敵,清軍步哨和山上機關槍猛烈射擊,經長時間仰攻,民軍苦不得登,仍退回花園。黃興以仙女山可瞰制漢陽,側擊大別山,非奪回不可,便決心拂曉進攻。
11月23日上午五時,民軍第七標自花園開始進攻,七時佔領仙女山東北;湯家山炮隊亦向仙女、美娘兩山射擊,清軍死傷甚眾,已現動搖。但民軍方面,因湘軍兩協逗留不進,第七標陷入孤立。黃興派人催湘軍向前,湘軍兩協仍不出一兵;黃興不得已,親往指揮。誰知第一協協統王隆中匿民房內,所部官兵已無鬥志;第二協協統甘興典擅離陣地,所部形同瓦解。黃興憤極,改派預備隊增援。時第七標統帶胡廷佐、管帶左國棟已受重傷,致無人指揮部隊。民軍又退守扁擔山、湯家山一線。
是日青山部隊渡江襲敵,海軍炮彈擊中敵陣。黃興得武昌電話,即以此鼓舞士氣,謂能奪回各山的,均有重賞。士兵們奮勇進襲,但登至山腰即為敵機關槍所擊退,傷亡很大。軍政府聞訊,軍務部通知各單位挑選精壯人員赴漢陽接戰,軍務部副部長張振武自任指揮,率眾夜半渡江,進入陣地,但已無法扭轉戰局,不久張振武因受傷返回武昌。
六、湘軍王、甘兩部擅自撤離前線
11月24日,漢陽戰況激烈,雙方都有重大傷亡。黃興因民軍各部長官多臨戰膽怯,甚至避不出戰,特傳知各部,如再發現畏縮不前者,無論何人,概以軍法從事。士兵有擅自退卻的,黃興立斬陣前,但仍無法挽回頹勢。當日,湘軍劉玉堂率一標來援,加入花園一線,進攻仙女山,仍未克。戰至午後七時,扁擔山、花園一線民軍失守。是晚總司令黃興在十里鋪宿營。
25日,民軍與清軍在十里鋪相持。正當戰鬥處在膠著狀態,民軍方面發生了重大事變,漢陽戰局隨之急轉直下。
該日上午,駐守漢陽的湘軍第一協統領王隆中擅自率部撤離前線,渡江至武昌兩湖書院集合。湘軍第二協統領甘興典見王部退走,也率部向漢陽鸚鵡洲方向撤退。正在十里鋪指揮戰鬥的黃興聞報,立即電話通知武昌方面。黎元洪得訊,立派蔣翊武、李作棟攜現金、酒肉,前往兩湖書院犒勞王隆中部,請其仍回前線,王隆中不允。黎元洪復派譚人鳳、李國鏞前往勸諭,李國鏞甚至長跪以求,王隆中仍不允。最後黎元洪在李作棟等人陪同下,親往敦促,並許以特別酬勞,王隆中悍然不應命。
翌日晚間,王隆中率部潛回湖南。湖北軍政府即電湖南都督譚延闓嚴懲王、甘。甘興典先到湖南岳州,被捕正法。王隆中聞訊逃匿。後來湘軍第一協在湖南改為第四師,王隆中仍當師長。
七、漢陽失陷前的死戰
湘軍王、甘兩部既去,前線民軍力量益見單弱,黃興恐漢陽不守,兵工廠為敵所用,決計將廠中重要機件和所存械彈運往武昌。當派正、副參謀長李書城、楊璽章渡江請示,黎元洪召開軍事長官會議,李書城發言,認為兵無鬥志,漢陽勢不能守,兵工廠機件應予拆運,楊璽章則力主死守,認為戰至一兵一卒亦不應放棄。會議最後決定,一面全力抗戰,一面搬運機件。楊璽章返漢陽督戰,李書城因連日作戰,困倦至極,留武昌休息一日。稽查部長蔡漢卿、軍務部副部長張振武率學生軍數百人隨楊璽章渡漢助戰。
同盟會員、在日本參謀本部研習軍事的夏道南此間返漢,奉軍政府命率部赴漢陽,在扁擔山、磨盤山一帶與清軍激戰三晝夜。
總司令部參謀甘績熙,時臥病武昌,聞漢陽危急,頓足忿呼,力疾而起,渡江見黃興,請挑敢死隊奪回已失諸山頭。黃興大喜,令甘績熙和朱樹烈自赴各營徵集。共得敢死士一百四十五人,於26日夜十一時由甘績熙、朱樹烈、孫宏斌、韓某四人率領前進,先襲磨子山得手,繼搶登扁擔山。黃興見山頭火起,立飭湘軍劉玉堂接應。磨子、扁擔兩山,復為民軍所有。甘績熙兩處受傷,劉玉堂要甘回後方,便請總司令派兵馳援。到漢陽前線採訪的《大漢報》主筆胡石庵對甘績熙的英勇戰鬥精神十分欽佩,作《甘侯行》贊曰:
「黑雲壓天黑風吼,百八健兒銜枚走;雄獅一奮萬怪逃,笑把芙蓉握兩手。如斯壯別問誰能,偉哉甘侯名穆卿!」
甘績熙返回漢陽,剛向黃興報告經過,前線傳來消息:扁擔山復失,劉玉堂力戰陣亡。此為11月26日晨二時事。
11月26日七時許,清軍由花園進攻十里鋪,正面用大炮密集射擊,迫民軍後退,且派奸細賄通民軍守黑山炮隊,黑山因以失守。十一時,民軍第三標管帶王殿甲陣亡。下午一時,楊璽章隨黃興在十里鋪督戰,楊忽遭一彈,貫腦而死。四時,十里鋪失守。
黃興知已無可挽回,當令塗金炳、羅子清等率輸送隊趕運兵工廠機件,王安瀾督率官兵搶運輜重。首義時率馬八標起事的漢川人祁國鈞(1889-1914),漢陽失守前夕,率部押運歸元寺總兵站物資,由十里鋪繞道大軍山,渡金口回武昌,減少軍事裝備的損失。漢陽失陷前,民軍又將漢陽鐵廠、兵工廠設備及零件拆卸,裝千餘箱,用渡船運至武昌平湖門外江邊,當時兵慌馬亂,無人看守、清理,湖北宜城人、參謀部恩賞課成員賈達孚「親督軍士、夫役等,逐一運至軍務部,並議集原有工人整修槍械,遂成立武昌兵工分廠。」
11月26日下午五時,清軍越十里鋪一線追擊民軍;礄口之敵用大炮轟擊敗退民軍,各部紛擾,無復統率。
黃興回到昭忠祠總部,哽咽說道:戰事一敗至此,眼見漢陽即失,實無面目見一般同志,惟有一死以謝同胞。經田桐等人哭勸,黃興乃收淚傳令漢陽各部作必要部署。歸元寺來不及運走的輜重,由黃興下令予以焚毀,免為敵用。黎元洪聞黃興憤不欲生,特派人過漢陽請黃興到武昌休息,黃興遂於11月26日十一時撤離漢陽。
11月27日晨,民軍繼續撤退。清軍由黑山向漢陽城挺進,民軍掩護部隊據城牆,邊射擊邊退卻。上午十時,清軍進入漢陽城內。沒有渡江的民軍部隊,則向鸚鵡洲方向退去,以後輾轉至大冶一帶,因無人統率,又無接濟,這支民軍多數散去。各地來漢投效之士,李儒清、王佐才、趙啟瑞、劉以東等,明知漢陽不守,猶自奮擊清軍,死而後已。留日士官生蕭鐘英,甚至於漢陽失守之後,仍自組敢死隊若干人,赴漢陽決戰。敵以機槍掃射,蕭鐘英和他的同伴無一生還。
總計漢陽之戰,自11月16日至11月27日,民軍共陣亡軍官137人,傷85人;士兵陣亡2693人,傷四百餘人。共計傷亡三千三百餘人。自武昌起義日起,至漢陽失陷,民軍英勇抗擊清軍凡48天。當民軍和漢陽百姓乘船向武昌撤退時,清軍從龜山向江中開炮,造成嚴重傷亡,「武昌城外,由江中撈出之死屍陳列堤上,不計其數。內有未死而呻吟者,有婦人抱子,母死而子蘇,啜泣索乳者。血濺江邊,死者相枕籍。」其狀極慘烈。
11月27日後,袁世凱從政治需要出發,基本停止軍事行動,並由「英國領事聯合各國領事,提議停戰三日,磋商條件」。以後,「繼又停戰七日,陽夏戰事遂由停戰延長而宣告結束」。攻佔漢陽以後,袁世凱奏請予前線清軍獎敘。馮國璋被賞給二等男爵,其餘如統制李純、王占元、陳光遠以及臨時擔任甲乙兩支隊長的吳金彪、馬繼增、張敬堯等,均有獎敘。清軍進攻漢陽,得到帝國主義分子支持的買辦的暗中效勞。歐陽萼即其一例。歐陽萼原系茶商,曾為布政使連甲所賞識,連甲逃出武昌即請歐陽萼為之籌畫一切。在陽夏戰爭中,歐陽萼又積極為馮國璋從外國人那裏籌集物資和經費。
陽夏戰爭期間,與帝國主義、買辦勢力支持清軍恰成對比的是,全國民眾以及海外僑胞援助民軍,各地種種志願戰鬥組織,競以決死、敢死為名參戰,要者如下:
一、鄂軍敢死隊
二、學生軍
三、童子軍
四、上海援鄂志願決死團
五、廣東決死隊
六、獨立將校決死團
七、特別義勇軍
八、陸軍特別同學後盾軍
九、遊擊隊
十、社會黨敢死隊
十一、南洋敢死隊
十二、江南敢死隊
十三、中央敢死隊
十四、中國學生決死隊
十五、橫濱敢死團
十六、戰時運輸隊
十七、湖北女子北伐隊
十八、學士軍
十九、和尚軍
二十、奮勇軍(一)
二十一、奮勇軍(二)
二十二、河南奮勇軍
第四節 海軍反正
一、黎元洪致書薩鎮冰
1911年10月12日,清政府下令海軍協同陸軍進攻漢口民軍。10月17日海軍提督薩鎮冰乘楚有艦抵漢,先後在陽邏停泊的艦隻有海琛、海籌、海容、楚同、江貞、江利、建威、建安、楚泰、湖鷹、湖隼等。

▲薩鎮冰像
10月18日清軍與民軍在漢口劉家廟大戰,薩鎮冰督率兵艦,防護江岸,阻塞民軍接應。瑞澂乘楚豫在江面遊弋。民軍向楚豫開炮,楚豫還擊,薩鎮冰指揮兵艦向民軍發射三十餘炮,民軍頗有傷亡。海軍少有革命黨活動,巡洋艦隊中「無一曾入同盟會之人」,然辛亥年間海軍官佐接觸革命書報,「勃然起革命之思」。
武昌起義後,海軍中一部分官兵正作回應醞釀,而且各艦乏米缺煤,對戰事取消極態度。民軍懾於海軍威力,正謀對策,恰在此間,黎元洪見民軍漸成氣候,於是對鄂軍都督一職的態度,轉變得較為積極。黎主動提出,他與薩鎮冰有師生之誼,黎元洪曾在北洋水師學堂機械科就讀,薩鎮冰是他的老師,可以致函示意。信寫好後,特請留美學生、基督教徒余日章送達,薩鎮冰未予回復。
幾日後黎元洪又作書致薩,由海軍投效人員朱孝先和黎玉山二人喬裝送達,附以犒勞物品。薩鎮冰璧還其物而受其書。據胡鄂公《武昌起義三十三日紀》說,黎元洪致薩鎮冰書,為孫發緒起草。然主持《大漢報》的胡石庵《湖北革命實見記》稱,八月二十九日(10月20日)上午八點鐘,「特別偵探黎玉山又至,出一函示余,蓋都督手書致薩鎮冰者,都千餘言,頗中肯綮。餘當抄發刊部登報,一面促黎迅投函艦上。」
由此可知,黎玉山在呈函薩鎮冰前,先將黎元洪致薩書交胡石庵看,胡當即抄錄並在《大漢報》印發。胡石庵強調該函為黎元洪的「手書」胡氏還作按語說:「此函確為黎公親筆書,不得以文章之優否觀也。」並言及「黎玉山上艦投函,頗受危險。及函投入,薩殊優待,並親書復函與黎,使攜之歸,並使人送登岸上。復函甚簡略,謂彼此心照,各盡其職云云,言外已有深意存也。」
同時,黎元洪還有致楚有、楚同、楚泰、建威、建安、江利各艦艦長書。此外,湯化龍曾致書其弟、時任艦隊代理參謀的湯薌銘,勸其策動海軍反正。薩鎮冰接黎元洪信後,曾有回復,原信失載。據傳說薩在回信中表示不忍見同種相殘,希能和平解決。同時他照常與袁世凱保持聯繫。10月28日(農曆九月十一),清軍進攻漢口,薩鎮冰曾以清海軍提督名義通知各領事撤僑,以便炮擊漢口民軍。是日下午三時,海籌、海容、海琛三艦自陽邏上駛,與民軍青山、兩望炮隊互擊。三艦共射七百餘發,未造成重大傷亡。此時薩鎮冰與民軍已有默契,各艦下級人員亦正多方聯絡,運動反正,惟都不便公開表示。11月1日各艦下駛,情形乃為之一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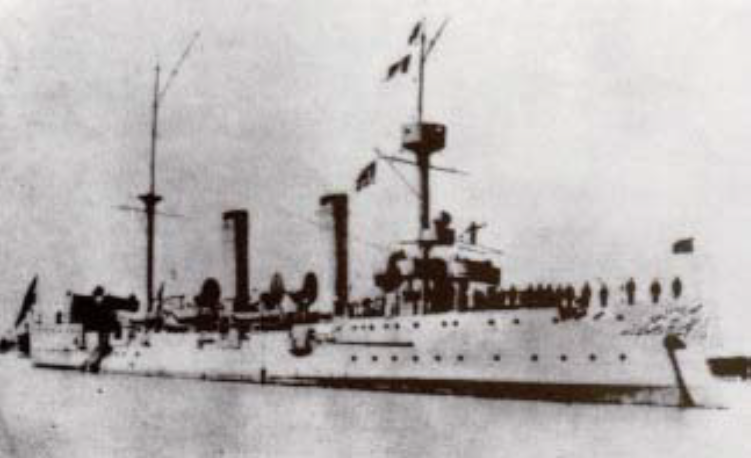
▲易幟後的海琛號軍艦
二、海軍醞釀反正和正式易幟
海琛艦正電官(電報通訊官員)張懌伯、海容正電官金琢章、海籌正電官何謂生,原屬同學,都具有革命思想,自聞武昌起義,即有反正打算。艦間禁止往來,彼此意志無由互達。何謂生利用電訊的方便,編英文密碼十二種,藉以溝通三艦消息。後海軍奉命進攻武漢,張懌伯即與駕駛二副楊慶貞、三副高幼欽、見習士官楊明數人,相機鼓動水手,以為助力。10月28日的青山炮戰,張懌伯即約同金琢章、何謂生,各向艦上炮手以人道主義相勸說,曾得到海籌艦沙訓齡、海容艦陳世英等人的同情,故發炮雖多,非指向天空即彈落水面。張懌伯以進行順利,暗中制一簽名單,贊成反正的簽名其上。海琛艦長榮續、海容艦長喜昌均滿人,雖與革命形同水火,然亦莫可如何。海籌艦長為黃鐘瑛,經何謂生進言,表示贊許反正,且予以便利,何謂生等因之更能大膽進行一切。
11月1日落旗時,楊明將海琛艦上的龍旗拋於水中,第二天改以白旗懸於艦尾。外國人記載說,清艦前掛龍旗,後懸白旗,不知為滿為漢。在艦隊反正過程中,這種情況確實是有的。飛鷹艦幫帶滿人吉升投江自盡。海容、海琛兩艦的艦長也在九江自動去職。
三海艦自湖北陽邏開抵江西九江,其時九江已經舉義,潯(九江簡稱)分府都督馬毓寶電告武昌:「本日(11月1日)午刻十點,有海籌、海容、海琛三戰艦到潯,據各船主云,系因水涸,奉薩統制諭命駛東下;並云薩統制與都督已有接洽。該船通豎白旗,並向潯軍分府請領國旗,惟窺其意,尚欲下駛。現在南京尚未克復,該船仍欲東下,不可不防。現已由潯將三艦扣留,暫不准下駛。究應如何處置及該艦需用煤米等,可否由潯供給,敬祈迅示遵行。」
黎元洪以為薩鎮冰必在此三艦上,復電馬毓寶予以優待。其實薩的座艦是江貞,三海字艦開往九江之後,薩鎮冰於11月13日自陽邏東行,經黃石港又改搭英太古商輪,轉赴上海。楚豫、江利、湖鵬等開往鎮江,有的則至上海船塢修理。薩鎮冰過九江時曾在英領事署寄宿一晚,他同各艦官員談話時略謂,本人廁身海軍垂三十年,屢歷戰爭,從未一獲勝利。現在同室相殘,即勝亦不足為榮;長此遷延,既無以對朝廷,更不便附合民軍。今以艦隊付君等,願君等好自為之云云。
其參謀官湯薌銘為武昌軍政府部長湯化龍的胞弟,湯隨薩停泊漢口,曾與乃兄通信,薩鎮冰從旁得知武昌一些情況。薩鎮冰離開艦隊,即由湯薌銘正式領導海軍回應革命。九江軍政分府則派林森、李烈鈞在招商局歡宴湯薌銘等。黎元洪在致電九江軍政分府都督的同時,又派李作棟持湯化龍信赴潯慰問反正海軍,並請其來鄂助戰。11月19日下午,湯薌銘、杜錫珪等率海容等艦上駛,仍泊陽邏。11月23日曾掩護青山民軍向諶家磯進攻。雖戰果不大,卻足以助民軍之氣而寒清軍之膽。
據湯薌銘(1885-1975)回憶,他把艦隊開到青山附近江面停泊,黎元洪派李國鏞攜帶銀幣若干發餉。當時海軍的任務是炮打二道橋和三道橋,配合青山民軍渡江,截斷漢口清軍歸路。民軍登陸以後,因缺乏訓練,人聲嘈雜,清軍炮隊射擊猛烈,雖經海軍火力壓住,民軍以地形不好,仍退回青山。後來黎元洪派人來請艦隊開到漢水入江處,炮擊清軍,阻其渡河進攻漢陽。湯薌銘即率海容、海琛西上,湖鵠魚雷艇隨行,與清軍沿江炮位互轟約兩小時,艦上有三人死亡,清軍第四鎮被擊斃三四百人。清軍據點在蔡甸,距漢水入江口六十里,海軍炮火不能達到,各艦便上下逡巡,不斷炮擊清軍在二道橋、三道橋和在江岸的工事。有些艦艇為清軍炮火擊傷,需要修理。加之入冬水淺,海容、海琛吃水較深,請准黎元洪開往上海。但據在海琛任駕駛的楊慶貞所記,到漢指揮作戰的為海籌艦長,被推任臨時隊長的黃鐘瑛,完全不涉及湯薌銘。張懌伯的《辛亥海軍舉義記》也只說到黃鐘瑛。
海籌下駛之後,即未再來湖北。11月25日黎元洪電九江都督馬毓寶:「懇速令海籌星駛來鄂接應,海容、海琛兩艦,望通濟兵輪轉運甚切,該輪及楚謙、楚觀、江貞三艦,頃究在何處,如均在潯,請並飭隨同海籌,刻即來鄂。」同日馬都督回電:「海籌在皖,業已派員赴皖,趕催該艦星夜駛鄂助戰。彈藥一節,早已電滬飭通濟速運往鄂接濟。江貞已載軍米赴皖。......楚謙、楚觀兩兵艦,刻下不知停泊何處。」11月28日,馬毓寶又電黎元洪:「催派海籌赴鄂助戰,均經轉催安慶,頃准皖都督李咨稱,上海水淺,海籌不能上駛。」
(未完待續)